我与中国的学术关系 |白乐桑:我学习汉语是因为
栏目:行业新闻 发布时间:2025-10-13 1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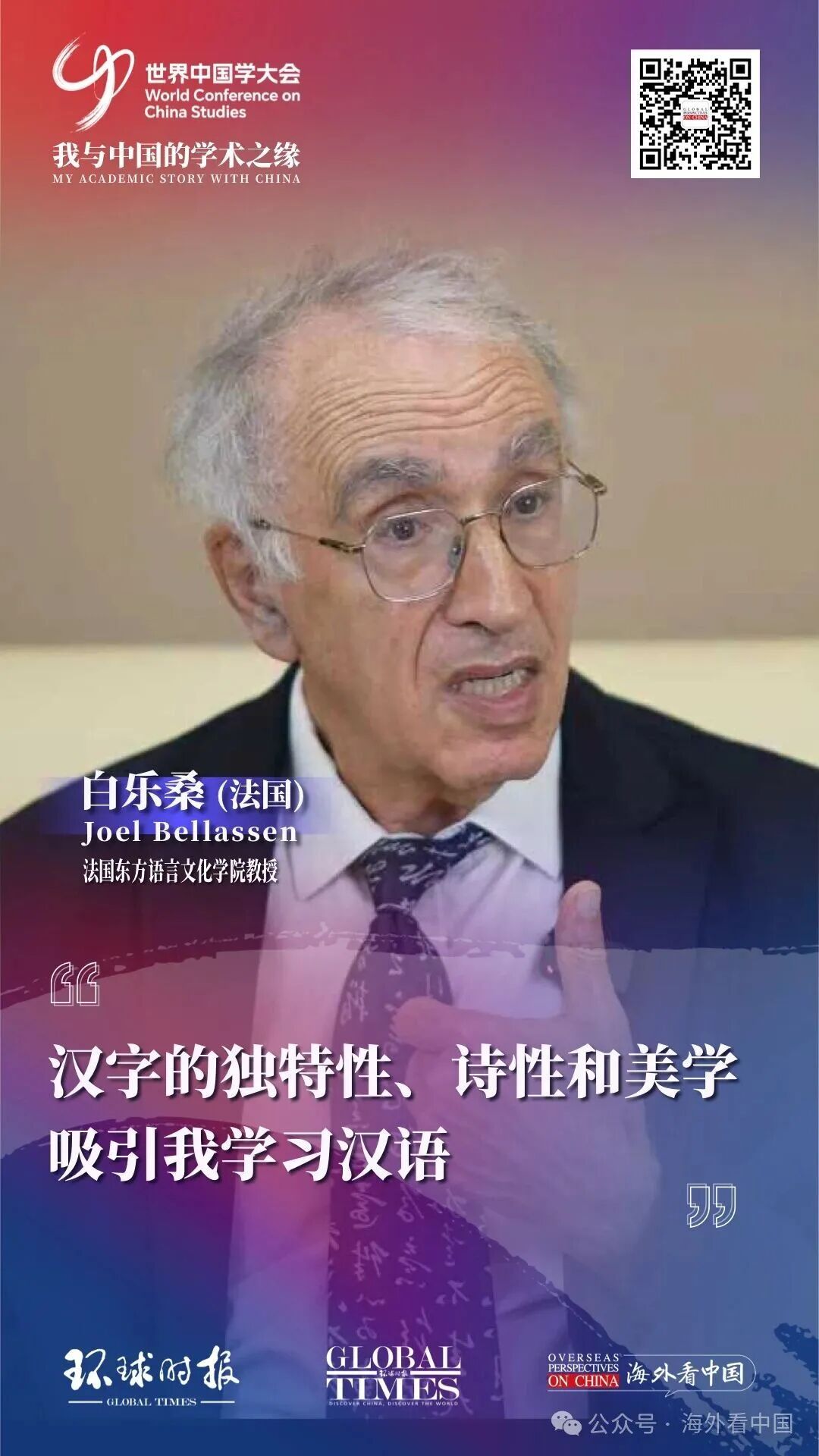 编者按: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向首届世界中国研究大会暨上海论坛致贺信,提出“中国研究是历史中国的研究,也是现代中国的研究”。为了提炼世界中国研究作为历史中国研究和现代中国研究的全球重要性和当代价值,在第二届世界中国研究大会召开之际,环球时报“海外看中国”工作室联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图书馆、上海社会科学院、北京语言大学合作推出“我与中国的学术关系”系列访谈节目。
采访:乔尔·贝拉森
环球时报:您的新书《汉语——表意文字的王国》的封面设计非常独特,融入了很多中国元素。为什么选择汉字作为封面设计的重点?
白乐桑:其实你可能不知道最古老的正规汉语第二语言教学机构诞生于法国。法国高等教育机构法国理工学院于1814年设立了华人教授职位,第一位华人教授是法国人莱姆沙。从那时起到今天,学习汉语的动机一直都很明确。汉字的独特性和魅力是很多人选择学习汉语的重要原因。
我自己也不例外。如果没有汉字,我今天可能就不会在这里,我也可能不会主修中文。汉字的独特性、诗意性和审美价值对于吸引学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基于这个想法,我曾经出版过一本以五十个汉字为主题的书,其中涵盖了表情符号、表意文字和语义字符。为了充分表达汉字的诗意和美学,我与画家合作,通过视觉艺术和文字的结合,重新表达汉字的诗意和美学。观众可以感受到汉字不仅是记录语言的工具,更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和艺术价值的文化符号。
环球时报:您认为语言和写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尤其是汉字,您如何定义它在语言系统和文化中的地位?
白乐桑:这是中心问题。世界学术界对语言和文字的定义有共识,但在汉字和对外汉语教学方面,教材众多,观点各异。尽管有些教科书认为汉字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但早期的法国观点认为汉字不仅是语言记录工具,而且是汉语独特的学术单位。
每个汉字背后都蕴藏着丰富的学术文化知识,使汉字教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不仅仅是补充语言的工具。例如,我曾经教授的汉字课程只需要几个小时来遵循通常的拉丁字母教学,但由于每个汉字都有历史、文化和审美价值,汉字课程可以持续一年或更长时间。我相信汉字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这就是它们如此重要的原因。
环球时报:您是怎么开始接触汉学的?为什么选择这个研究方向?
白乐桑:首先我想谈谈我对国学的理解。汉学不仅是研究汉语的学问,而且是研究汉语的学问。是知识,是中国的方方面面,包括人物、文化。早期的汉学家大多是传教士(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当然还有法国人),他们也是汉学的学者和重要创始人。
他们研究中国园林、建筑、文学、礼仪等各个领域,帮助欧洲世界了解中国的独特之处文化。例如,法国学者帮助欧洲学术界了解苏州园林。否则,欧洲人很难进入这个充满异域风情的文化世界。
20世纪中叶,“Sinology”强调专业化、系统化,逐渐演变为英文的“Sinology”。学术领域不断发展,涵盖甲骨文、儒家经典、现代文学、中国美食等多个领域。就我个人而言,我有幸能够在法国参与中国教育和汉学的研究,这让我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产生了研究的兴趣。
环球时报:您在学习期间参与过很多科研项目。您能告诉我们一些您最难忘的经历和挑战吗?
白乐桑:我曾在法国教育部工作,负责国家的汉语教育政策。这是一个妈妈cro 和具体任务。任期内,我在法国中小学基础教育体系中首创了汉语课程“汉语国际班”。这就需要与中国教育主管部门密切合作,确保课程内容与法国教育体系保持一致,体现汉语教育的学术深度。
我们还参与推广汉语水平测试的活动。自1994年在法国举办首届汉语水平考试以来,每年举办一次,直至今日。这些项目不仅是教育实践,也是科学研究探索的一部分。他还积极参加学术会议和学术领域发展,推动汉学和汉语教育的发展。
环球时报:根据您的观察,世界范围内中国的汉学研究现状如何?
白乐桑:在近几十年来,中国汉学和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以法国为例。五六十年前,巴黎大学中文系只有六名学生。然而,我现在所教的汉字班通常有超过 100 名学生。在教育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学校开设了正规的汉语课程,学生从中学甚至小学就开始学习汉语。在高等教育中,汉语的实用价值和就业潜力被广泛认可,因此不仅汉语系增设了课程,一些商学院也开始开设汉语课程。
即使在学术界,研究也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例如,法国有三四位神谕研究者,研究古典、现当代文学的学者数量不断增加。去年,一位法国汉学家普嘎哥对这个故事的史上最完整、最专业的翻译,展现了中国文学在国际学术界日益增长的认可度和影响力。
环球时报:您之前提到过烹饪和国学之间的关系。您能否介绍一下近年来中国研究跨学科拓展的情况?
白乐桑:这当然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比如,一位20世纪70年代跟随我到北京学习中文的同学说,她虽然是国学博士生导师,但她的研究领域是中国饮食文化和烹饪史,而不是语言或文学。在法国,饮食文化是职业教育的重要领域,也是学术研究的领域,但在中国尚不普遍。
此外,我个人的研究方向还包括语文教育主题化。 1997年,我成为E第一人欧洲获得汉语教育博士生导师资格,建立了汉语教育学科独立的研究与教学体系。我指导的第一个博士生获得了学位,这也表明汉语教育在法国正在逐渐发展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中国电影、文学等文化现象也被纳入教学和研究,体现了中国研究的跨学科趋势。
环球时报:您认为国际经验能给法国汉学研究带来哪些启发?
白乐桑:我一直认为学术交流很重要。如果学者不与其他国家的同事互动,他们很快就会落后。不同国家的见解和观点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汉学。
例如,对于汉字的性质就有不同的看法。我相信汉字是一个学术单位习惯于汉语,但在汉语教育国际化中,理解和研究的方向不同。中国教育史与汉学史的主题归属也存在争议。我倾向于认为生物学应该被视为中国教育领域的一个分支,就像生物学史是生物学的一部分一样。通过国际交流,我们可以就这些根本问题达成更大共识,促进学术发展。
环球时报:请概括一下您个人与中国学者的命运以及这种命运所带来的学术知识。
白乐桑:我与中国学者的关系始于我对汉字的好奇。汉字的独特性、诗意和文化深度促使我从事中国研究。从最初在法国接受汉学教育,到参与汉语教学、国际课程和跨学科研究,我见证了世界汉学和中国学的专业化、系统化发展。
对我来说,汉学不仅是一门学术研究,更是一座文化桥梁。通过汉学的学习,我们了解中华文化的深度和审美价值,让世界认识到中华学术和文化的独特魅力。我们希望这种学术关系能够继续促进跨文化交流,让更多的人体验到汉字之美和中华文化的丰富。
编者按: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向首届世界中国研究大会暨上海论坛致贺信,提出“中国研究是历史中国的研究,也是现代中国的研究”。为了提炼世界中国研究作为历史中国研究和现代中国研究的全球重要性和当代价值,在第二届世界中国研究大会召开之际,环球时报“海外看中国”工作室联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图书馆、上海社会科学院、北京语言大学合作推出“我与中国的学术关系”系列访谈节目。
采访:乔尔·贝拉森
环球时报:您的新书《汉语——表意文字的王国》的封面设计非常独特,融入了很多中国元素。为什么选择汉字作为封面设计的重点?
白乐桑:其实你可能不知道最古老的正规汉语第二语言教学机构诞生于法国。法国高等教育机构法国理工学院于1814年设立了华人教授职位,第一位华人教授是法国人莱姆沙。从那时起到今天,学习汉语的动机一直都很明确。汉字的独特性和魅力是很多人选择学习汉语的重要原因。
我自己也不例外。如果没有汉字,我今天可能就不会在这里,我也可能不会主修中文。汉字的独特性、诗意性和审美价值对于吸引学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基于这个想法,我曾经出版过一本以五十个汉字为主题的书,其中涵盖了表情符号、表意文字和语义字符。为了充分表达汉字的诗意和美学,我与画家合作,通过视觉艺术和文字的结合,重新表达汉字的诗意和美学。观众可以感受到汉字不仅是记录语言的工具,更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和艺术价值的文化符号。
环球时报:您认为语言和写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尤其是汉字,您如何定义它在语言系统和文化中的地位?
白乐桑:这是中心问题。世界学术界对语言和文字的定义有共识,但在汉字和对外汉语教学方面,教材众多,观点各异。尽管有些教科书认为汉字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但早期的法国观点认为汉字不仅是语言记录工具,而且是汉语独特的学术单位。
每个汉字背后都蕴藏着丰富的学术文化知识,使汉字教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不仅仅是补充语言的工具。例如,我曾经教授的汉字课程只需要几个小时来遵循通常的拉丁字母教学,但由于每个汉字都有历史、文化和审美价值,汉字课程可以持续一年或更长时间。我相信汉字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这就是它们如此重要的原因。
环球时报:您是怎么开始接触汉学的?为什么选择这个研究方向?
白乐桑:首先我想谈谈我对国学的理解。汉学不仅是研究汉语的学问,而且是研究汉语的学问。是知识,是中国的方方面面,包括人物、文化。早期的汉学家大多是传教士(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当然还有法国人),他们也是汉学的学者和重要创始人。
他们研究中国园林、建筑、文学、礼仪等各个领域,帮助欧洲世界了解中国的独特之处文化。例如,法国学者帮助欧洲学术界了解苏州园林。否则,欧洲人很难进入这个充满异域风情的文化世界。
20世纪中叶,“Sinology”强调专业化、系统化,逐渐演变为英文的“Sinology”。学术领域不断发展,涵盖甲骨文、儒家经典、现代文学、中国美食等多个领域。就我个人而言,我有幸能够在法国参与中国教育和汉学的研究,这让我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产生了研究的兴趣。
环球时报:您在学习期间参与过很多科研项目。您能告诉我们一些您最难忘的经历和挑战吗?
白乐桑:我曾在法国教育部工作,负责国家的汉语教育政策。这是一个妈妈cro 和具体任务。任期内,我在法国中小学基础教育体系中首创了汉语课程“汉语国际班”。这就需要与中国教育主管部门密切合作,确保课程内容与法国教育体系保持一致,体现汉语教育的学术深度。
我们还参与推广汉语水平测试的活动。自1994年在法国举办首届汉语水平考试以来,每年举办一次,直至今日。这些项目不仅是教育实践,也是科学研究探索的一部分。他还积极参加学术会议和学术领域发展,推动汉学和汉语教育的发展。
环球时报:根据您的观察,世界范围内中国的汉学研究现状如何?
白乐桑:在近几十年来,中国汉学和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以法国为例。五六十年前,巴黎大学中文系只有六名学生。然而,我现在所教的汉字班通常有超过 100 名学生。在教育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学校开设了正规的汉语课程,学生从中学甚至小学就开始学习汉语。在高等教育中,汉语的实用价值和就业潜力被广泛认可,因此不仅汉语系增设了课程,一些商学院也开始开设汉语课程。
即使在学术界,研究也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例如,法国有三四位神谕研究者,研究古典、现当代文学的学者数量不断增加。去年,一位法国汉学家普嘎哥对这个故事的史上最完整、最专业的翻译,展现了中国文学在国际学术界日益增长的认可度和影响力。
环球时报:您之前提到过烹饪和国学之间的关系。您能否介绍一下近年来中国研究跨学科拓展的情况?
白乐桑:这当然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比如,一位20世纪70年代跟随我到北京学习中文的同学说,她虽然是国学博士生导师,但她的研究领域是中国饮食文化和烹饪史,而不是语言或文学。在法国,饮食文化是职业教育的重要领域,也是学术研究的领域,但在中国尚不普遍。
此外,我个人的研究方向还包括语文教育主题化。 1997年,我成为E第一人欧洲获得汉语教育博士生导师资格,建立了汉语教育学科独立的研究与教学体系。我指导的第一个博士生获得了学位,这也表明汉语教育在法国正在逐渐发展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中国电影、文学等文化现象也被纳入教学和研究,体现了中国研究的跨学科趋势。
环球时报:您认为国际经验能给法国汉学研究带来哪些启发?
白乐桑:我一直认为学术交流很重要。如果学者不与其他国家的同事互动,他们很快就会落后。不同国家的见解和观点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汉学。
例如,对于汉字的性质就有不同的看法。我相信汉字是一个学术单位习惯于汉语,但在汉语教育国际化中,理解和研究的方向不同。中国教育史与汉学史的主题归属也存在争议。我倾向于认为生物学应该被视为中国教育领域的一个分支,就像生物学史是生物学的一部分一样。通过国际交流,我们可以就这些根本问题达成更大共识,促进学术发展。
环球时报:请概括一下您个人与中国学者的命运以及这种命运所带来的学术知识。
白乐桑:我与中国学者的关系始于我对汉字的好奇。汉字的独特性、诗意和文化深度促使我从事中国研究。从最初在法国接受汉学教育,到参与汉语教学、国际课程和跨学科研究,我见证了世界汉学和中国学的专业化、系统化发展。
对我来说,汉学不仅是一门学术研究,更是一座文化桥梁。通过汉学的学习,我们了解中华文化的深度和审美价值,让世界认识到中华学术和文化的独特魅力。我们希望这种学术关系能够继续促进跨文化交流,让更多的人体验到汉字之美和中华文化的丰富。 下一篇:没有了
